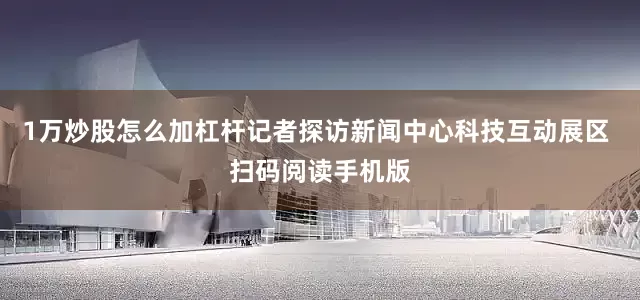复生不易
作者|张光渝
潘复生身为山东籍人士,早年以济南乡村师范学生的身份投身党的地下斗争,于1932年不幸被捕。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共识。韩复榘政治犯获释,潘复生出狱投奔抗日战场。(相关阅读《汪曾祺:韩复榘“诗人”》《韩子华问:蒋介石为何杀韩复榘?》)
1945年,父。张霖之自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之位晋升,转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的政治委员,同时担任军区司令员一职。杨勇奉命接任第七纵队的司令之职。与此同时,冀鲁豫区的党委及军区亦完成了相应的改组工作。张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赵健民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潘复生担任区域党委副书记及组织部部长之职。此乃解放战争初期,冀鲁豫根据地主要领导团队的成员名录。
1956年八大,杨勇、张玺、赵健民、潘复生和我父亲张霖之成为73名中央候补委员之一。
1949年8月,潘复生任新成立的平原省委书记新乡市,作为平原省的省会,见证了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所承载的12年辉煌历程的圆满结束。踏入1950年之初,濮阳地区不幸遭遇了因组织失误导致的民工与马匹冻毙的悲剧事件。濮阳运粮事件”。当时纪律很严格,潘复生因负领导责任,降为省委副书记。
这只是小挫折,1952年。张玺调至新国家计委。潘复生接棒张玺,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一职,而吴芝圃则担任河南省省长。这位省长在政界颇具影响力。
1957年,在潘复生在省委会的领导下,河南省委出台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力争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提纲》。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当时提出采用奖励机制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这一举措深受群众的热烈欢迎。然而,这一政策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并不相符,那时正值政治上开展反右派运动,经济领域也正酝酿着“大跃进”的到来。时任省长……吴芝圃积极发起反驳,指责那份宣传提纲充斥着“右倾情绪”与“保守主义”的倾向。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省委的第二把手启动了针对省委第一把手的全省性批判活动。在八大二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同时,亦提及“潘复生虽犯过失,然应给予他改正的机会”。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隆重召开,标志着“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启动。吴芝圃反右有功,邓小平对吴芝圃言:“真理显然掌握在你们手中。”会晤结束后,潘复生被解职,下放到农场劳动,吴芝圃任省委书记一手导演河南“大跃进”。
吴芝圃孕育了我国首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敢于提出连毛泽东也难以全然信任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主导了覆盖全省的反右倾政治浪潮,因不同意高指标和高征收政策,导致数以万计的干部和群众被打死、打伤或被捕入狱;从公社到县市各级行政干部、群众,被错误地指控为“小潘复生”者高达二十万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严峻的时刻,吴芝圃仍旧虚报粮食产量,将河南的粮食产量240亿斤夸大至400亿斤,即便在上百万民众饿殍遍野的情况下,他仍隐瞒真相,欺骗中央,最终酿成了轰动党内的“信阳事件”。最终,毛泽东亦感忍无可忍,吴芝圃于1962年遭受撤职处分。调任中南局担任“文教书记”以了此一节。吴芝圃在致党中央及中南局的检讨书中坦诚,其错误导致了“信阳事件”的发生。灾难惨不忍睹”,“欠五千万,债一辈子还不起。”。(相关阅读《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事件》)
1962年4月,中央批准潘复平反潘复生履新的职位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社长。虽然这个职位看似“闲散”,却对潘复生具有非凡的意义,标志着他在政治生涯上的“重生”。自此,他由河南步入京城,成为一名朝廷官员。
北京市副市长万里送长子赴京锻炼。潘复生我向老战友推荐了自己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县黄河滩畔的农场。自此,“万老大”便在那片土地上担任了十几年的农工。
1966年1月,潘复生被任命为黑省委第一书记他又一跃成为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然而,若历史可以倒流,我想潘复生宁愿选择在那个“社长”的闲职上悠然度日直至退休。
1966年9月至12月,父。张霖之疗养于黑龙江三个月。潘复生在那个纷繁复杂的境遇中,对我父亲予以格外关照,实属不易,更显其仗义精神。
作家梁晓声在20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书中披露了他少年时期在黑龙江度过的那段“文革”岁月。对于这部作品,我并不发表个人评价,但他对于“文革”初期情景的描绘,却是真实而深刻的。潘复生这位自称“正在养病”的副省长,实则被造反派所操控。潘复生被推向前台,扮演“革命领导干部”的角色,仿佛辛亥革命起义军中所担当的。黎元洪将床底下的物品随意拖拽,仿佛视其为总统之尊,这种说法纯属误解。
1967年1月16日,事实上,潘复生在坚定支持之下,黑龙江省的23家单位纷纷组建了造反团,并正式成立了联合总部,随后发布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潘复生因最早对红卫兵运动表示支持,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其声名远扬,蜚声全国。。
《人民日报》载文热烈庆祝黑龙江省“革命政权”的成立,标题为《喜迎黑龙江省革命政权诞生,共筑伟大事业新篇章》。东北的新曙光该报发表的社论《西南的春雷》,与为贵州夺权之举所撰写的同名文章遥相呼应,一时间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回想起往昔,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经历“夺权”之后,荣任首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堪称首开先河。,后来还有河南的刘建勋和广西的韦国清。
潘复生得以占据此高位,客观上或许源于他在1966年刚履新职,与黑龙江省委先前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无瓜葛,这使得他易于表达立场,且反动团体亦乐于接纳。然而,在“文革”结束后仍能稳固地位的,唯有他一人。韦国清一人而已。
1967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一场夺权的风暴横扫全国,势不可挡,正如古人所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月3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潘复生任省革委会主任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也历经长途跋涉,我从沈阳抵达哈尔滨,特地前来参加成立大会,并致以诚挚的祝贺。
革命委员会自当秉持“革命”之精神,而革命之举必有所指,目标明确。黑龙江首“革命对象”为潘复生前上司东北局第二书记、黑省委原第一书记欧阳钦。欧阳钦的独子欧阳湘未曾承认其父系“三反分子”身份,1968年11月,化名“洪新建”向省革委会投书,力挺欧阳钦,力阻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在潘复生的批示下,“洪新建”旋即被捕。当年,《黑龙江日报》以通栏标题形式,报道了针对欧阳湘的群众宣判大会。
竭力为被诬称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刘少奇及其代表辩护,并为之鸣不平、招魂平反的,正是以“洪新建”署名投递反革命匿名信的我省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欧阳钦之子,欧阳湘。
被捕后的欧阳湘被迫害至死,年仅28岁。
潘复生曾被自己的搭档吴芝圃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未及数年,却反遭前任第一书记的指责。欧阳钦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称号,竟致这位资深同志的独子丧命。此类“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同走马灯般轮番更迭的情景,无疑揭示了个人责任与品德的问题。然而,若将此类悲剧反复上演的原因简单归咎于个人,显然是不够的。
潘复生的“革命”立场并未使他得以保全,至1970年7月,终究未能幸免于难。周恩来明确指出:黑龙江问题的根源,实则深植于潘复生之身。。
1971年6月,潘复生免职事实上,他已远离工作岗位将近一年之久。导致他倒下的原因诸多,其中包括因过往被捕的经历而被诬为“叛徒”,然而这并非源于他参与推翻欧阳钦的事件,更非因欧阳湘的离世。欧阳湘直至1978年方才——胡耀邦在亲自督促下获平反。即:潘复生在黑龙江遭受颠覆之时的成因,实则并非我们现时所认为的他的那些过失。这是历史的偏差。
在“文革”期间,任何领导人都无法规避这场运动的考验。即便你秉持常规思维,遵从党的指示,积极支持群众运动,也难以避免犯错的命运。在这场运动中,无论个人身份如何,要么在初期遭受打击,要么在中期遭受批判,要么在后期面临审查。
我父亲张霖之那时看透,便与母约定。活着就是胜利。
这番话适用于张霖之,也适用于潘复生,此规定适用于除少数特殊情况外的所有地方领导干部。在我父亲完成在东北的疗养,即将离开哈尔滨返回北京之际,在与潘复生告别时,他又一次说道:可杀我,但不可诬我反党。。
此言乃是对“活着即是胜利”的进一步阐释,它是我父亲所确立的坚守底线——无论遭遇何种境遇,他都决不屈服于内心的诱惑,承认自己有悖于党的立场。同时,他与母亲携手立下誓言,共同承诺“绝不轻生”。潘复生认为父亲之言过于严峻,彼时他未曾深思,若自身再度倒地,是否仍有望“重生”。。自哈尔滨一别,两位老战友的命运各异:我父亲沦为革命的“目标”,而潘复生则成为了革命的“推力”。回首往昔,几十年的时间流转,他们最终都成为了“文革”这场荒诞闹剧的无辜牺牲者。
潘复生政治上未再崛起经过长达九年的严格审查,潘复生在1980年因抑郁而离世。回顾过去,似乎在“文革”初期虽被倒台却未丧命,反而成了最好的结果。然而,这种微妙的分寸感实属难以掌控,又有谁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潘复生逝世两年之后,中共中央于1982年4月正式批准了黑龙江省委对其审查结果的认定。经核实,历史问题已明确无误。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将不进行组织上的处理。。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重生”吗?五十年前因革命被捕,五十载光阴逝去,却在逝世后两年才被确认“无过错”,这种境遇怎能不令人痛心?我母亲在“文革”期间曾向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如此对待被俘的革命者,恶劣影响不可小觑,亚非拉地区的革命者目睹被捕释放后仍遭受不公待遇,还有谁愿意投身革命?
1979年,中央隆重举办了一场八人联合追悼会,中南局书记亦出席其中。吴芝圃的遗像和我父亲张霖之遗像并排悬挂,静静地等待着众人一一致以鞠躬之礼。此刻,正处在审查中的潘复生定能在报纸上寻觅到这一篇报道,目睹了张霖之和吴芝圃同台举行的告别仪式,潘复生心中会涌起何种情感?潘复生离世时并未得出定论,因此未曾有公开讣告发布。吴芝圃追悼会举行,潘复生讣告不发。。
通常而言,黑龙江的干部普遍对潘复生持有负面评价,认为他过于“左倾”,极尽偏激之能事。老干部整老干部”。然而,在河南,情形却大有不同。河南民众对潘复生在“大跃进”时期遭受吴芝圃的打压,怀抱着深深的同情。2006年,一部著作问世,其中便详细记载了这一段历史。治河六十年》中就有一节题为“怀念潘复生同志。河南铭记老书记。
1968年,潘复生自黑龙江赴京参会,我陪同母亲一同前往京西宾馆探望他。彼时的潘复生看似一位健壮的中年男子,实则已逾六十。母亲一见到潘复生,便忆起与丈夫在东北共度的最后岁月,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放声痛哭。潘复生轻声安抚,口中不断重复着我父亲临别时留给他的话语。那幕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恒汇证券-中国十大股票软件-买股加杠杆-十大优质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